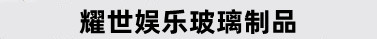我们每天都在跟光学材料打交道——眼镜上的镀膜、手机和电脑屏幕里的光学膜、光通信、光纤、光计算等等。我们也期待增强现实(AR)的发展,光学材料与结构正是AR技术的基础。由果壳发起的未来光锥前沿科技基金,投资了一家研发光学材料的企业“天璇新材料”,最近,未来光锥与天璇新材料创始人周宓博士做了一场对话。
天璇新材料已于 2023 年完成天使轮融资,并将于近期开启新的一轮融资,如有意可于文章末尾添加团队联系方式。
周宓:感谢未来光锥给我们的这个机会。我是80后,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海归创业者,2010年从新加坡国立大学物理系博士毕业之后,加入了全世界最大的化学材料公司之一巴斯夫,一待就近十年时间。中间轮过好几次岗,2010年到2013年我在巴斯夫新加坡做研发,后来公司要建立亚太区的电子材料商务中心,负责公司电子材料相关产品。
在首尔除了本身的产品开发之外,也负责跟像韩国的三星、LG,也包括日本和台湾地区的一些企业打交道。2016年,又把我从亚太区的总部调到德国总部工作,负责全球产品线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,算是比较完整的经历。
我是在19年回国的,先加入了宁波卢米蓝新材料,做OLED发光材料。这家公司是我的老师、一个院士的团队创立的,我负责公司新产品线开发,也负责公司的投融资,几年时间销售成长了将近20倍。
到了2022年的8月,我觉得自己也更成熟一些了,就从卢米蓝出来创立了天璇新材料,老东家也支持也作为股东支持了我的创业。
周宓:今天的天璇核心是在光学材料,更具体的说是光学界面材料。就是通过折射率、微结构,通过吸收谱系等手段,去调控光的方向跟强度,解决光在不同介质界面的传输问题。我在巴斯夫工作的时候,特别是在德国期间做很大的一块就是光学材料领域强相关,这对我现在的工作也有很强的借鉴和指引性。
吴云飞: 我们有很多角度去理解光,不过我好奇对于你这样跟光打了20年交道,你眼中的光是什么?
周宓:好久没有听到这样触及灵魂的问题了。我们都学过波粒二象性之类的概念,光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能量,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反应。在底层逻辑上来说,我们做光学材料,就是在控制光的能量的分布。它可以是在单一方向上的能量分布的递进,也可以是在不同角度上能量的分布。我举个例子,比如芯片的加工是需要浸润技术的,这就是要通过调整浸润液的折射率,让光从镜头出来的时候,能更好的聚焦去生产半导体。
吴云飞:这个举例就特别有意思,出现在了平时不太容易被联想在一起的领域,那你们目前主要做的是什么方面?
周宓:光学材料应用的场景非常丰富,光纤通信、激光器,也包括大多数涉及显示的事情都会相关。
我们自己现在产品分三大部分。一块就是光纤光通信。像特种光纤里的涂层,包括我们做光纤进入光芯片的接口,也需要有特种的涂层和胶水在光芯片里面的一些微结构。
第二块我们做的是微纳光学。传统光学很长时间没有去被特别改造过了,比如凸透镜凸面镜。我们现在做折射光学和衍射光学,就是把折射率进一步提高,把尺寸从毫米级做到纳米级。
第三块,也是现在相对比较走量的,就在做泛显示领域里面包括薄膜上的特种涂层和微结构相关产品。
周宓:从材料端的角度来说是有很强的底层技术相通性的。再往上看,从毫米到纳米一个尺度上去衡量,本质上回到了光的基础的物理特性,就像刚才讲的那样。
吴云飞:材料类的创业,就特别怕把事情给做窄了,不过你描述了好几个完全不同的场景,但底层又相同,是不是这就解决了成长空间的问题了?
周宓:成长这一块我也确实不担心。我在这几年整个的行业的发展中,能深刻感受到产业界对光的研究,和信息技术一直在互相推动。我举个例子,比如大家现在常讲的AI,就促进了光纤和光通信的发展,即使在今年相对低迷的二级市场里,相关公司股价其实都涨得挺好的。而且能看见很多还没落地的新场景也在不断涌现,我自己的感受是很有生命力的。
现在做创业团队也不容易,既要脚踏实地拿订单,也要仰望星空对未来的三年,五年做些预判,等事情完全成熟再去做的话,就会很难去超越很多本身资源很丰富的大公司了。
周宓:作为公司来说,我觉得做高大上的创新技术的同时,最好在早期也能些现金流,这对包括生产、品控、销售队伍的团队锻炼来说,都是很重要的事情,这就有一些能够相对快速进入市场的产品先跑。而且,不同行业导入周期是不太一样,比如光纤光通信它验证周期比较长,常见可能18个月24月,但薄膜行业整体验证周期就会比较短一些,6到12个月就够了,我本身也有不少商务积累。所以有跑量的产品带着,让不同领域导入时间窗口过渡更平顺。
吴云飞:光学薄膜产品已经有一些龙头公司了,那么你们往这里走进去的思路是什么?
周宓:具体的薄膜产品,国内的确已经有龙头公司有在做这块,但对应的高端功能涂层涂料大部分还是用国外的产品。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国产化替代,这里面首先会有一个降本的逻辑,这在如今的环境下其实非常重要。另外我们能响应客户,配合客户产品开发的速度,大家还是比较欣赏的。国外的公司,特别是有些通过代理商合作的公司,跟国内下游客户的研发速度是无法匹配的,我们正好去有机会去弥补这个空白。
吴云飞:我们接下来说一下仰望星空的部分,你们的材料涉及很多场景的应用,我猜AR(增强现实)移动显示这一块是尤其会被关注的,能不能请你讲讲对这一块的理解?
周宓:AR是现在我们在微纳光学范围内的主力的产品。我觉得在围绕着AR尤其是衍射光波导这个主流技术路线来说,在国内公司里面很有自信的说是一流的,也有不少客户反馈我们是做的最好的。不算吹牛,在短短两年时间内能够达到这个高度,我自己对团队还是很自豪的。
吴云飞:对于AR,我觉得行业里面非共识的地方还挺多的,你对这个方向的市场预期如何?
周宓:我自己在显示行业经历过从LCD到OLED迭代的完整周期。从创新的角度来说,这十年的发展我觉得的确是进入了瓶颈期。市场上期待着一个新的终端的产生,能够引领产业的突破导,从而再进一步推动商业端的进步。
我跟国内外很多厂家都也交流过,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共识是目前的AR形态并没有被确定,就是现在的产品还没有定型,但它已经是走的最远的一个了,背负着最多厚望的产品了。横向和VR产品相比,VR产品在今年一季度比去年大概有10%左右的销售降幅,但AR产品出货量比同期增加了60%,这还是一个在消费低迷的时期里完成的成绩,我觉得他的成长性是非常可以被期待的。
吴云飞:提一个不太准确的对比,比如你觉得AR能达到现在智能手表的市场规模吗?
周宓:我觉得智能手表还是作为表的替代品,负责的新功能会比较少一些。但我对AR眼镜的期待,是提供一个完全全新的交互方式,人类90%以上信息就是通过眼睛摄入,戴眼镜的人,包括未来戴AR眼镜的人未来获取世界信息的过程就会通过这样一个产品,从这个点看,没有别的选择。我觉得业界共识是AI的发展将给AR眼镜很大创造新的赋能,它天生更适合处理视觉信息,这让他有机会能够去开发新功能。
市场整体的爆发是需要周期的,但如今的市场反馈,包括今年 Meta 和雷朋合作的眼镜达到了百万出货量,这让大家觉得行业的tipping point(引爆点)会比我们之前想象的会更早一些,比如26年应该就能冲到1000万台以上的规模。这里面硬件本身,配套软件的发展,和爆款产品或事件的推动都很重要。
吴云飞:你从世界龙头企业,走到国内龙头企业,再到了明星创业公司,现在是一家三十多人创业公司的创始人。就感觉就像你在升级打怪,节奏有条不紊一步步设计到这来的?
周宓:我其实没有特别这样想过,比如我在毕业的时候其实没想过创业的事。但现在看来,似乎真是冥冥之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里,这应该是性格使然。之前每一段的经历都让我觉得学到很多。今天我们的整个产品设计的理念,包括公司管理的理念,都是当年在大公司承接下来的,不过我把它本地化,变成了更适用于初创型公司的东西。
我公司刚刚成立20个月,但我跟团队说的是,要把天璇也做成百年老店,百年老店很重要的点,就是要在早期就建立好规范和文化,让团队能够传承和迭代下去,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。我跟新员工都是这么讲的,希望公司能一代一代传承下去。跟同事开玩笑的时候,我们说希望能够在这里退休,说不定以后大家的小朋友也能在这上班。耀世/注册平台,对话天璇创始人周宓:AI与AR都离不开的光学材料。